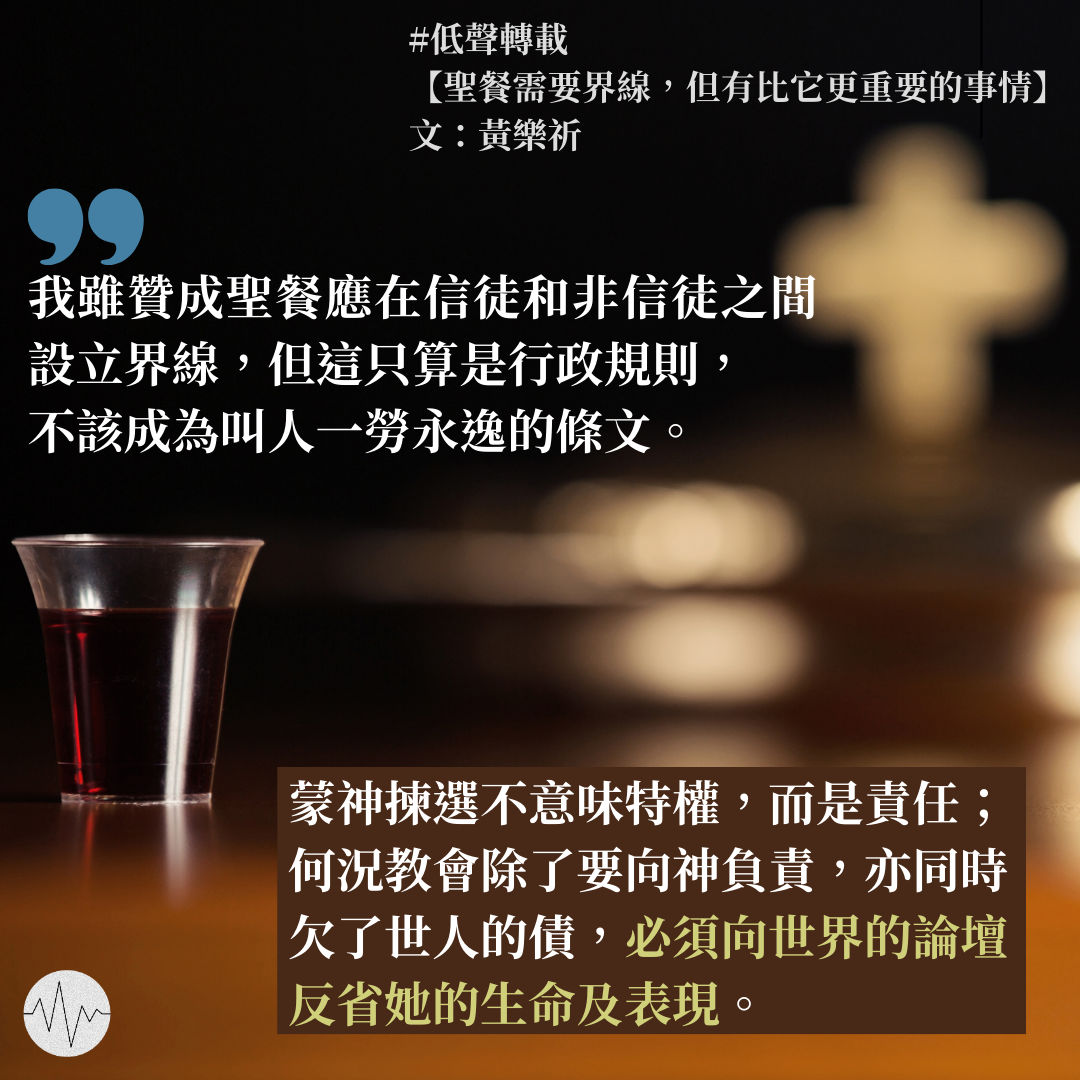黃樂祈:聖餐需要界線,但有比它更重要的事情
「基督徒會嚴肅的進行對話,因為他知道自己的說話可能會因個人的傲慢、固執、虛假的自信和攻擊性而受到損害,並淪為社會的謊言。他將永遠承認自己也是一個罪人,因此將在對話中有關自己的部分交予上帝的審判和憐憫。」[1]
德國中部,馬爾堡(Marburg)。城中有一個小山丘,聳立了一座顯赫的城堡。1529年10月,馬丁路德(Martin Luther, 1483-1546)和慈運理(Huldrych Zwingli, 1484-1531)在那裡因未能就聖餐觀(天主教譯作「聖體聖事」)達成共識,不歡而散,此事對往後整個宗教改革運動的影響可謂極為深遠。可見,聖餐觀單是在新教各個派系之間都可以成為爭論不休的原因,更不用說新教群體如何在這個聖禮理解與羅馬天主教、正教的關係。這也許提醒我們,討論聖餐在教會歷史總是敏感的、需要再三謹慎的。
▍ 討論界線牽連者不只聖餐論
如是者,教會關於聖餐論的爭辯不是現代才橫空出世——總有人把較為他們眼中激進的想法與定義不明的「自由神學」扯上關係。關於非信徒領受聖餐的討論,在教會歷史中早已出現過。[2]可以說,在聖餐這個「聖」禮上,信與非信之間是否存在一種屬靈的楯檻,從來不是一種「不證自明」的議題。我認為,這可以作為眾人思索楊思言博士謂「與其問『誰人有資格領聖餐』,不如也問『誰人有資格將障礙放在別人腳前,阻撓人到主前呢』」的起點。[3]
作為受造物,教會曾在生命和上主之間擺放過(而且還在擺放中)各種錯誤的障礙,這是不爭的史實;然而,在聖餐的討論中,是否需要因此把鐘擺調至另一種極端,主張否定所有的範疇呢?這方面,除了較為人熟悉的「上帝的臨在」、「紀念主」等向度,我認為其中一個值得參考的觀點乃「聖餐作為一種審判(judgement)」。我必須強調這只是一個觀點,因為任何意圖說服他者接受一套「正統的」聖餐觀往往是徒勞無功的,諸如一位新教徒希望說服一位天主教徒不要相信變質說(transubstantiation),或者西方傳統去向東方傳統闡釋聖餐用的餅不應有酵等等。[4]
那麼,何謂聖餐包涵終末—審判的意義呢?倘若絕罰(excommunication)此一牧靈行動(最理想的情況下)與領受聖餐早於初期教會時期已息息相關,且到今日在不少教會紀律中仍然存在「暫停領受聖餐」的項目,我們似乎有需要考量聖餐與信徒分別為聖歸神——以及延伸出關於聖餐與非信徒朋友——之間的關係。[5]如果真的無人有資格為聖餐設立某種界線(即或這種界線基於教會的受造性而在上帝面前絕非完美),我們可能就需要繼續追問,例如:是否要否定教會執行紀律的任何可能性?會否屏棄了信仰群體存在某些秩序來規範的需要?
▍ 潘寧博對莫特曼認為聖餐「作為公開邀請」有所保留
但是,我不認為教會能全然忽視德國新教神學家莫特曼(Jürgen Moltmann, 1926-)在其著《聖靈大能中的教會:論彌賽亞式教會論》(1975)第5章「在聖靈臨在中的教會」中所提倡的「聖餐應該是一種『公開的邀請』」。聖餐的分歧往往讓教會分裂而非合一的教訓,乃莫氏反思聖餐觀時的出發點之一,[6]是我們需要正視的。
莫氏看來並不完全接納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基督宗教神學家之二,即拉納(Karl Rahner, 1904-1984)和巴特(Karl Barth, 1886-1968)的聖禮觀,因為他認為聖禮無論建基於教會和基督論,都仍然存在排他性的危險,[7]致使聖餐不能向基督的死與復活所指向的和好對象「世界」敞開,[8]及把教會扭曲成為自己而存活的教會,而非聖靈中的教會。[9]因此,在他的釋經中,「萬軍之耶和華必為萬民擺設宴席」(賽25:6-8),以至耶穌白白的、出人意表的接待罪人,與他們吃飯(路15:2),都證明主的饗宴不是排他的義人「飯局」,而是尋找失喪之人的盛宴。[10]
我認同教會時常會陷入一種自義、排除異己的試探,但是否代表耶穌與罪人吃飯,等於直指聖餐應該無條件向所有罪人(世上沒有一人不是罪人)開放?那麼,我們該如何理解那個幸運被邀請參與喜宴,卻因不穿禮服而被捆起手腳並扔在黑暗(太22:10-13)的無名氏呢?基督改變那些被祂改變名字的人,但不信者卻(暫時)不會接受這個規範,[11]這個應該是我們需要留神之處。
因此,即或莫氏不覺得「為的是紀念我」(路22:19;林前11:24)、「新約」(林前11:23-26)與公開饗宴有衝突,[12]試問非信徒的朋友真的可以認同——或準確點說,「相信」——三一神的工作嗎?畢竟,「相信基督」不意味人就變成義人,相信基督的人仍然是作為罪人(只是被算為義)、不配的人受邀,但他們被要求穿上禮服,好去參與上帝主動為眾人擺設的宴席。宴席固然向善惡者都公開,卻不代表主人對應約者毫無要求——恩典不是廉價的。
也許這解釋了潘寧博(Wolfhart Pannenberg, 1928-2014)何以對前同事、對談夥伴、朋友的莫特曼[13]之聖餐觀有所保留時,表示「那些在耶穌的聖餐中尋求與祂相交的人必須想要(want)這種相交」,[14]又引用了《十二使徒遺訓》九章5節:「除了奉主的名受過浸/洗的人之外,無論甚麼人都不許領受聖餐。」[15]這種意願(willingness)的表態,或者我們可以用「穿上禮服參與宴會」此一舉動來理解。
▍ 聖餐界線不意味「『合資格』基督徒」擁有某些特權
可是,說到這裡,我認為教會應該要從三十年戰爭(1618-1648)後出現的敬虔主義對新教正統主義的批判得到一些啟發:生命應該高於教義;沒有重生的稱義是虛構的(fiction)。[16]如果我們不反對神學不是一種沒有重生的人都能參與的客觀科學,[17]教會當下真正需要的就先是對重生的關注,而不是獨立於生命的純粹聖餐理論。我們不要忘記,《馬太福音》22章喜宴比喻那個不穿禮服而遭趕出的人,也可以意指宗教領袖和對神不忠的信徒。[18]同理,如果聖餐真的與審判相關,保羅要求哥林多信徒在聖餐前應省察自己(林前十一27-34)顯然是向信仰群體說的。就連潘霍華(Dietrich Bonhoeffer, 1906-1945)論到廉價福音包括「領聖餐而不需要懺罪」之際,[19]亦是批判教內的文化。
是以,我雖贊成聖餐應該在信徒和非信徒之間設立界線(有些教會甚至要求只有已接受浸/洗禮者才能領餐),但這條某程度算是「行政規則」者,不該成為一種迷信、叫人一勞永逸的條文,讓人錯覺以為表面「合資格」的施餐或領餐者之生命必然能在神面前站立得穩。「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,人若不重生,就不能見神的國。」(約3:3)
倘若我們認為聖餐需要有一條「信與不信」的界線,教會必須躬身自省:我們真是相信基督嗎?我們真是已經在聖靈裡重生嗎?我們真的有省察自己的屬靈基礎,以致我們可以在聖餐中正確紀念主(in remembrance of Jesus Christ)及祂與我們所立的約,使我們一再意識到主的臨在和救贖行動嗎?[20]我們的行事為人真的與所蒙的呼召相稱(弗4:1)嗎?還是,我們也不過只是「不信」的一份子?潘寧博說得坦白,信仰和生活有所聯繫的門徒訓練(discipleship)才是參與聖餐的前提(prerequisite)。 [21]
教會可以不完全認同莫特曼的聖餐觀,不過也無需否定他的提醒:基督徒的生命最重要的,始終是一種持續學習基督的生活風格。[22]復興—更新不可能是紙上談兵的;[23]對教義適當的執著,不可能與生活割裂。任何試圖假扮被聖靈轉化的偽善終會被揭露出來,因為人不可能「自我製造」與主連結才可有的生活風格。[24]
從這個層面來看,聖餐觀未必是重中之重的問題——傳統的貴格會(Quakers)甚至是禁止(prohibit)聖餐的;[25]救世軍(The Salvation Army)迄今仍然不舉行聖餐禮。所以,假若教會群體未能活出一種因基督的犧牲而應有之改變,[26]這條不結果子的枝子只能被剪掉並扔進火裡燒(約15:1-6);這堆失了味的鹽只能丟在外面,任人踐踏(太5:13);這種無行為的信心是死的(雅2:14-26)。
我們就算真要談「聖餐的界線」,必須同時緊記美國神學家韋利蒙(William H. Willimon, 1946-)之勸勉:蒙神揀選不意味特權,而是責任。[27]何況教會除了要向神負責,亦同時欠了世人的債(羅1:14),必須向世界的論壇反省她的生命及表現,[28]難道我們還未覺悟,自己原來需要認真反省外界對教會行事為人之觀感或反應嗎?要記起主曾對以色列說:「在地上萬族中,我只認識你們;因此,我必懲罰你們一切的罪孽。」(摩3:2)
注釋:
[1] Karl Rahner, Karl-H. & Boniface Kruger trans.,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, Vol. VI: Concerning Vatican Council II (London: Darton, Longman & Todd, 1969), 1:3.
[2] George Hunsinger, The Eucharist and Ecumenism: Let us Keep the Feast (New York: Cambridge University, 2008), pp. 70-71.
[3] https://www.thevoicehk.com/news/20231114-1
[4] A. Edward Siecienski, Beards, Azymes, and Purgatory: The Other Issues that Divided East and West (Oxford: Oxford University, 2022).
[5] John D. Zizioulas, The Eucharistic Communion and the World (New York: T&T Clark, 2011), pp. 28-31.
[6] Jürgen Moltmann著,曾念粵、杜海龍譯,《聖靈大能中的教會:論彌賽亞式教會論》(香港:道風,2019),頁299-301。
[7] 同上,頁248-250。拉納提出教會本身就是「救恩的基本聖禮」,巴特則認為基督就是「那聖禮」,或「第一個聖禮」。
[8] 同上,頁302。
[9] 同上,頁253-255。
[10] 同上,頁304-305。
[11] P. J. FitzPatrick, In Breaking of Bread: The Eucharist and Ritual (New York: Cambridge University, 1993), pp. 155-156.
[12] Jürgen Moltmann,《聖靈大能中的教會》,頁307。
[13] Jürgen Moltmann, Steffen Lösel trans., “Personal recollections of Wolfhart Pannenberg,” in Theology Today, Vol. 72, No. 1 (2015), pp. 11-14.
[14] Wolfhart Pannenberg, Geoffrey W. Bromiley trans., Systematic Theology, Vol. 3 (London & New York: T&T Clark International, 2004), pp. 329-330.
[15] Ibid., p. 327.
[16] Carter Lindberg ed., The Pietist Theologians: An Introduction to Theology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(Oxford: Blackwell, 2005), p. 6, ref. 46: Martin Schmidt, Pietismus (Stuttgart: Kohlhammer, 1972), p. 14.
[17] Paul Tillich著,尹大貽譯,《基督教思想史》,二版(香港:道風,2005),頁410。
[18] Craig A. Evans, New Cambridge Bible Commentary: Matthew (New York: Cambridge University, 2012), pp. 378-379, ref. 471: D. C. Sim, “The Man without the Wedding Garment,” in Heythrop Journal, Vol. 31 (1990), pp. 165-178.
[19] Dietrich Bonhoeffer著,鄧肇明、古樂人譯:《追隨基督》(香港:道聲,2013),頁11-13。
[20] Craig A. Evans, New Cambridge Bible Commentary: 1-2 Corinthians (New York: Cambridge University, 2005), pp. 98-99.
[21] Wolfhart Pannenberg, Systematic Theology, Vol. 3, p. 330.
[22] Jürgen Moltmann,《聖靈大能中的教會》,頁337-338。
[23] 同上,頁341-342。
[24] 同上,頁353。
[25] Timothy Burdick & Pink Dandelion, “Global Quakerism 1920-2015,” in Stephen W. Angell & Pink Dandelion ed.,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Quakerism (New York: Cambridge University, 2018), p. 40.
[26] Craig A. Evans, New Cambridge Bible Commentary: 1-2 Corinthians, p. 99.
[27] William H. Willimon著,黃杰輝、阮雅瑜譯,《上帝多奇異:韋利蒙論揀選、使命與宣講》(香港:基督教文藝,2017)。
[28] Jürgen Moltmann,《聖靈大能中的教會》,頁7。